
在读学校:The Hotchkiss School
录取学校: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我喜欢看向未来,然后寻找意义,赋予意义,并以此为前行的动力。而早在申请美高那年的元旦,好朋友的爸爸就提醒过我:别忘了脚下的路。
关于时间
作为一个资深拖延症患者,我总是幻想着某一天,自己可以用坚韧的毅力去战胜拖延,走上人生巅峰。然而那时的我尚未意识到,拖延这项活动着实是一样奢侈品。2019年秋季,我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没有时间拖延——毕竟当每天都有三四个deadline逼近眼前时,每分每秒都是拖延到最后一刻极限完成的感觉。在我的日程表里,时间从以月为单位到周,再到天,再到只希望完成每一个小时。
3:30 pm,下课,从教室赶回宿舍,处理白天的邮件,换衣服赶往曲棍球场训练
5:30 pm,曲棍球训练结束,跑回主楼参加辩论队训练以及其他社团活动
10:00 pm,活动安排妥当,门禁前赶回宿舍,与品优沟通或视频
11:00 pm,开始作业
2:00 am,作业少的话,睡觉
3:30 am,作业多的话,睡觉
7:00 am,作业多的话,起床补作业
8:10 am,作业少的话,起床准备上课
拿着我一天仅有的24小时,double shot咖啡,和能量棒,我以小时为单位度过了整个11年级和12年级的秋季。期间我关于时间的理解是那么模糊,以至于现在回忆起来像是400多天都混杂成了同一天。但在一片混沌中,有些细节我还能清晰的回忆。比如凌晨3点去走廊里接水时,迎面走来的同学和我互相笑着鼓励一番,各自也还清醒的穿着还没时间换的校队体育服。比如深夜与老师讨论完文书后,电话挂断前她叹气,说“囡囡你还是要睡一点啊”,然后沉默。比如曲棍球训练后跑回宿舍的路上身边的人和我忽然驻足,分出十几秒仰望雨后彩虹,然后再匆匆赶往下一个活动。
当时间被切割成碎片时,我很难透过它们去看清更加宏观的愿景,其中的尴尬就像是试图用二维单位去丈量三维空间。但我曾依然挣扎着为每一篇碎片赋予意义,即使身心俱疲。每一天凌晨,摊在床上入睡前,我都忍不住质问自己,我付出的时间到底是为了达到什么?我的目标在哪里?每一天我都答不上来自己的提问。
于是我慢慢的明白了,有些时候你就是要低着头走,一步一步,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的走。当我看不清前方的路时,那就看向脚下,每一步都走好。最后回头一望,倒也行了千里路。
关于努力
训练狗狗的流程其实总结起来也很简单。指引狗狗作出指令的动作后,迅速给予奖励,然后以此重复直到让它们知道指令完成后即可享用美食。说起来有趣,我在训练自家狗子的时候曾以为世间多数努力都基本如此,一个任务对应一块奶油小饼干。当然,在我眼里,我的小饼干自然是多种多样的,不论是实际的奖励还是自身人格和能力的提升,都算是努力应得的回报。
这个信条一直都是我不断探索各个领域的主要动力之一,因为不管最后拿到了哪块“饼干”,我总能把它看做奖励。然而大学的申请却不会这么善解人意的给每个孩子都分配“训导员”,也没有类似“握手”、“坐下”,这类明确清晰的指令。但最令人晕头转向的,是这整个过程对于“回报”的局限性。每个人都迫切的想要知道通往名校的公式——参加校报还是学生会,选修希腊还是拉丁,PS是卖惨还是强行幽默。
在这样的大趋势下,私立寄宿高中,带着它名字中就有的使命感(preparatory school),架起了一热锅。锅下烧着家长与孩子们共同的名校梦,锅中炖着各种乱七八糟的配方,锅上蒸发着冒着泡的焦虑。而我也不能免俗。渐渐地,我不知不觉中对努力的回报有了非常明确的定义:好大学。我的“小饼干”慢慢只剩下了一种,就是所谓可以帮到我升学的。而其他的奖励,比如磨练出的对于美国政治的了解,比如对音乐与美的思考,比如躲在厕所里哭完后继续回到训练的坚持,都似乎失去了它们以前对我的吸引力。在这口沸腾的焦虑下,似乎这些模棱两可的奖励都在现实的升学问题中显得多余且无奈。
11年级下半学期,我时常感觉自己就在那口锅里随着同龄人的焦虑一起沉沉浮浮。从10年级入学开始,我便一直有一个现在都记不起为何的执著:我要做一个理科生。但令人焦虑的是挂着理科生招牌的我在Physics C和线性代数的成绩都实属惨烈,而活动又看上去七零八乱,又是辩论又是作曲。第一次和顾问老师聊天,我说我想升工院,她沉默。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时的执著好笑,但其实那时的我真得考虑过为了缓解焦虑而摒弃个性,把自己挤进一条“明路”。我记得我焦虑地问顾问老师,“我这样的孩子怎么办呢?”感觉我所有的努力都零零散散,连不成章。她说,但你完成的东西就是完完全全关于你的,它们可能连不成一个标准爬藤的活动范例,但它们可以完完整整的代表你。
现在看来,我对美国政治的了解就是我的芝加哥大学论文的顶梁柱,我对音乐与美的反思就是我PS的中心主旨,而我擦干眼泪后的坚持就是我贯穿所有申请所传达的精神。最后,这些看似无关的“小饼干”都串了起来,把我一路领到了offer面前。但其实真正的顺序是这样:用心努力后得到的奖励由不得我去挑选,但它一定会有。而这些我发自内心努力得来的成果,就是我申请的独一无二的配方。
关于勇气
又或者是关于任性。在美高的这三年,我着实坚持了一些十分任性的选择。比如即使一年多都毫无成绩但还是不退辩论队转向其他活动;比如执意要在11年级选全校最难的物理数学和历史课程外加3门其他课程;比如在学校顾问建议ED2 NYU和BU时坚持说我要申请芝加哥。而这些选择其中有些是不计后果的愚勇,有些则是孤勇。申请ED2芝加哥,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孤勇。
孤勇中,“勇”是勇气的勇,“孤”却不是孤单,而是被包容的孤注一掷的任性。
其实芝加哥很早就是我和顾问老师商量出的perfect match之一:从最开始知道的奇奇怪怪的文书,到后来了解的芝加哥大学“大胆”的不限于政治正确的学术风气,这一切都是和我认知的自我所匹配的。然而即使早早就定下了ED2芝加哥,我的ED1不尽人意的录取和学校升学老师的多次劝阻都让我不禁一次次质疑我的选择。圣诞假期初,我惶惶地拿着学校老师推荐的选校清单去见顾问老师们,上面推荐ED2的选校气得她们花容失色。看着生气的她们,我却十分不合时宜的笑开了,因为我透过她们愤怒的背后轻松地看到了她们对我坚定的信心。于是我便有了底气,笑着任性道:“我喜欢芝加哥,我想ED2我最喜欢的。”“好,你喜欢我们就一定要升,你整个人就是匹配的!文书第二稿写起来吧”,她们坚定的说道,于是我笑着重回了心无旁骛的改文书循环。完整地传达信任,有时倒也不需要过多的语言。
 品优创始人Anson老师
2020-07-15 10:55:37
品优创始人Anson老师
2020-07-15 10:55:37


 FindingSchool美高排名
FindingSchool美高排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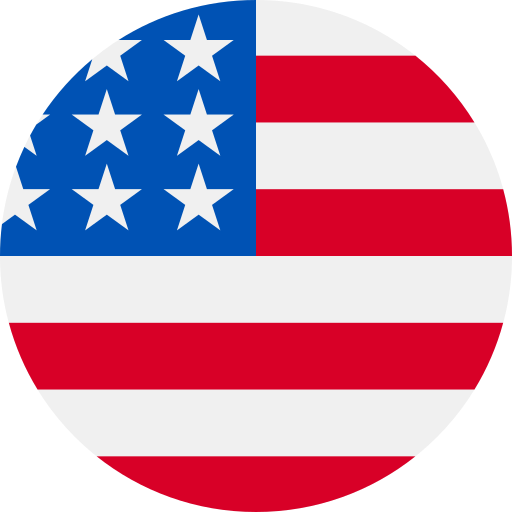 美国
美国
 加拿大
加拿大
 英国/瑞士
英国/瑞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