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awrenceville南瓜妈
2013-04-28 16:36:18
Lawrenceville南瓜妈
2013-04-28 16:36:18
父女两地书之给女儿的信(选八)
女儿:
想和你聊聊我最近的读书心得。 这几天我在读一本书,中文名叫《大数据时代》,副标题是《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英文名是《BIG DATA》,副标题是《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Work,And Think》。作者是英国人Viktor Mayer-Schonberger和Kenneth Cukier。据译者介绍这本书是讲大数据的最权威的作品。 读关于大数据方面的书,是受了我上海的朋友陈晓明先生的影响,从一个投资银行家的角度,他告诉我未来的社会是个大数据的时代,而这一行业也是有广泛的发展前景。 我当然对投资银行一窍不通,但本着“众好之必察焉”的古训,更何况是好朋友“好之”?于是到网上搜罗了一些关于大数据的书回来。 你知道我一直以来看人文科学方面的书籍比较多,兴趣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学和军事,古今中外都喜欢,但关于科学的书籍看的不多,所以脑子其实是很陈旧的,对最新的科学和技术了解上慢一拍。比如,玩手机微信,如果你不教我,恐怕我到现在还不会。这一点你老妈比我强多了,她对最新的东西感觉比我快,脑子也很“活络”,所以我也要补补这方面的课。 看了书才知道,不光是时间、空间、地球、文本、音像等可以数据化,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原来我们毫不关注的那些细微末节,我们认为是自然而然的被丢弃的东西,我们认为是生活的小浪花(或许连浪花都不算只能说是小波纹)随便他奔腾向前东流入海,甚至我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这些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都可以被很容易地收集并且数据化地保存起来。那些我们平时根本不屑一顾的东西当成千万上亿次的被重复的时候,其产生的效果,其产生的价值简直令人难以想象,确实象书的作者说的,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事实上大数据已经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了),相比之下,商业利益仅仅是这一大变革的附属物而已。 我们平时通过微博等社交工具进行的交流,我们手机上发出的每一个信息,都被那些谷歌,Facebook,Twitter等公司有意识的收集起来了并数据化,而且被有效地利用,其用途之广泛令人匪夷所思,真是应了那句话“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说来也可笑,而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些东西聊过就丢掉了呢,当然我也知道一些云空间之类的东西可以保存资料的(我和朋友们的评书资料交流就是通过云空间进行的),问题是我一直觉得象微信上的那些无聊的废话根本就没有保存的价值。 现在看来我的想法是错的。 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技术,而是意识,为什么要保存这些东西?应该如何有意识的保存和利用?这种意识是如何培养的? 一直以来中国的理想主义教育就喋喋不休地告诉我们,一切要向前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是不是错了?值得深思。 涉及到商业和技术上的事情我不是太懂,但从我这个历史学者的角度出发,我感觉这个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会改变我们历史学的未来。 就拿中国的历史来说吧,梁启超曾评价说:一部煌煌二十四史就是历代帝王的家谱。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只有帝王将相的言行被记录下来成为可供后人研究和书写的原始资料(当然考虑到当时的记录和储存手段,这也仅仅是一些片段),后来写历史,不论是正史还是戏说,不论是文本还是音像,都只能以此为蓝本,根本无法越雷池一步。比如楚汉相争,再现代的手法,再夸张的联想,也还是围绕这项羽和刘邦两个人做文章,说到底,还是在续写那些“家谱”。 中国的历史对帝王将相的记载都非常详细,有一种编年体史书叫《实录》,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最早的实录是南朝梁的《梁皇帝实录》,记载梁武帝一朝事。明清以后的实录大都保存着,前几年流行的一本叫《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书,就是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参阅了《明神宗实录》后写的,资料非常扎实。还有一种更夸张的宫廷记录叫《起居注》,顾名思义,就是皇帝每天吃喝拉撒那些事。后来的正史,基本就是参考这些实录和起居注等而来的,可见,要想不写成帝王家谱都很难。 而大量的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所思所想根本就不可能被记录和保存,甚至根本就没有人想着去保存,只能甄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帝王将相舞台上的一道淡淡的背景。尽管都承认“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但显然人民不是历史编纂学的主角。 人类的不平等在历史编纂学中体现的最明显,而这种不平等反过来又加剧了人类本身的不平等,循环往复。 中国的官修史书是在官方组织下编撰,并受到严格监控,什么东西能写,什么东西不能写,哪些史料能用,哪些史料不能用,都不是由历史学家说了算,而是由官方意识形态,或者说是帝王的个人喜好说了算。某种程度上说,一部正史完成的过程也是大量史料被甄别和毁灭的过程(特别是那些涉及宫廷隐私和朝代更替的部分),破坏和建设一样地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功能,在御制的《资治通鉴序》里说的很清楚: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敎,断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一大推话说到底还是为了统治的需要,一切有利于统治的都保留,乃至褒奖,而一切不利于统治的全部剔除,甚至在根本上予以否认存在,这个在中国历史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孔子作《春秋》,就是“笔削”为之,结果据说达到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最高功能:“乱臣贼子惧”。至于史料的真伪,增删是否合理,那都属于小事,就是假的又能如何?我们现在文艺作品中津津乐道的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尽管她自称为帝,又改国号为“周”,但在中国传统史书上根本就没人承认她是皇帝,历史上也没有一个叫“武周”的朝代,在两唐书的作者看来,武则天先是唐朝皇帝的老婆,后来又是唐朝皇帝的母亲,后来又是唐朝皇帝的祖母,除了李家人,还能是什么?所以在《旧唐书》和《新唐书》里标准称谓是则天皇后,简称武后,这就叫盖棺定论。 对于后来的人们来说,真实的历史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成文的历史文本,那些“人心中的历史”才会对后来者起到褒奖、示范和威慑作用,这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极终追求。 中国的传统几千年来一贯就是在各个方面都是“下层学上层”,“上有好着,下必甚焉” ,就比如现在一个再穷的人,也一定是买了一栋纸扎的别墅而不是经济适用房去祭奠他的死鬼老爹,同样,要买个小丫环去阴间伺候他的话,那一定长得象范冰冰而不是凤姐。 从这一点上看,明清时代那些家谱的作者真的很好地理解了中国纪传体史书的精髓。在家人眼里,一本家谱就是一部家族的正史,能上家谱并被记录下来的差不多就等于上了列传。在中国有句老话,叫“死者为大”,岂能不认真对之?于是,增删篡改者有之,涂脂抹粉者有之,以至于我们现在去读那些明清时代的家谱,那些谱主们一个个都是那么地道貌岸然,仿佛都是具体而微的帝王将相,煞有介事。 悠悠两千年,一样的河流一样的水。 就算是上了正史,里面的记载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也是干巴巴的,要么煌煌诏书冠冕堂皇,要么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要么对外和亲对内残暴。总而言之,你很难在里面看到一个正常的社会是如何运转的,这个社会的普通百姓是如何生活的,除了造反和镇压,你也很难看到传统社会是如何互动的。甚至那些帝王家谱的谱主们,也是面目模糊,要么圣人,要么魔鬼,要么先圣人后魔鬼,要么先魔鬼后圣人,反正没有一个是正常的人。 这也很正常,一个停滞了两千年的社会很难要求他有什么活力,更不可能产生什么近代的市民社会。 这一点在唐宋以前更明显,那时除了官修的所谓正史以外,流传下来的大都是一些文集,诗词歌赋,毕竟文章受到的限制要比历史书少一些,而象《世说新语》这样的笔记体的纪实文学作品,则少之又少,以至于我们现在研究六朝以前的历史,文集是很重要的史料,基本通过诗词歌赋来推测当时一些著名人物的喜怒哀乐,来给正史那一堆骨头里填补些血肉,文不仅用来“载道”,还能用来“识人”。比如,如果曹操的全部诗文没有流传下来,那我们现在该怎么理解孟德,大军阀?京剧大白脸?还是《三国演义》里的奸雄? 当然能流传下诗文的也是那些帝王将相,王孙公子,而且也是挂一漏万的。 唐宋以后,随着印刷技术的提高,文人的笔记流传下来的就比较多了,对正史也增加了不少补充,让后人对当时社会的了解也全面了一些,但是王朝史的模式没有改变,一直到现在。 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中国存在,西方史学界也存在的,罗马时代普鲁塔克的《英雄传》差不多也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这是时代的限制。 历史学家一直以来的最大困惑就是无法找到能真正体现社会意志,或称为“民意”的资料来反映一个社会的全面状况,或者只能用官方意志来代表民意,或者只能用被扭曲的所谓民意来代表真正的大众的民意,或者只能用抽象调查的方式通过样本来推测民意。当然这里除了官方压制以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技术手段的不足。我们很难想像在传统技术条件下每个人在没有外力的迫使下,对任何问题都自由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被记录下来。 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技术保证正在使这一天慢慢到来,博客、微博,微信、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工具使得人们可以很轻松地自由地发表意见,并且能被保存下来且统计出来,就像随口说一句话那么地简单。然而对这些杂乱无章的数据的归类和总结,将变成一种真正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学家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资料,它反映的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社会和它的一切活动,在这种确凿无误的历史资料面前,所有的谎言将再也没有容身之地。 这样一种真正的以全部人类的活动为基础的历史学将诞生,历史学将彻底摆脱帝王将相的历史而回归大众的历史,到那时我们才可以说,普通民众登上了历史学的舞台。 如果我们进一步推论的话,还可能会打出更让人吃惊的结果。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历史结论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大的方面说是阶级意志或群体利益的的体现,小的方面说是历史学家个人的偏好,总之,纯客观的历史学还没有出现。 但是如果用大数据来统计一个群体的所有方面活动的话,那么,结果就是把人类的活动完全的数据化,这些完全不带有任何的价值判断的数据将构成我们未来历史学的基础,那么这种由冷冰冰的数据构成的历史学还是文明熟悉的历史学吗?我们还需要历史学吗?有统计学就够了吧,历史学家的工作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统计学家的工作。 或许是我想多了,或许真有这么一天。 这就是我读这本书时联想到的一些和历史学有关的思考,其实关于大数据和我们的生活,我还想到很多,但都是一些火花,无法写下来,只能以后当面聊了。 不管怎么说,技术进步正在加速改变我们这个世界,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希望你在加强人文科学学习的时候,一只眼睛也要盯着最前沿的科学和技术进步,这一点在美国会更容易地获取,只要结合的好,传统和时尚并不矛盾。 下次在和你聊聊以前读过的一本***的小说,想和你聊聊***的那些事。 每天睡个好觉。 老爸 2013/4/26
[登录后评论]
-
写得太好了, 期待聊聊文革的那些事!

 FindingSchool美高排名
FindingSchool美高排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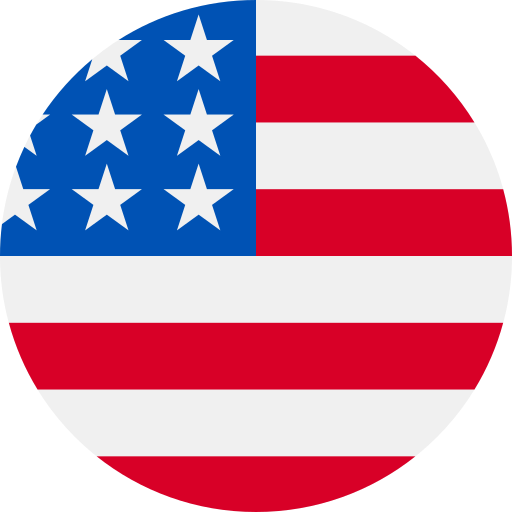 美国
美国
 加拿大
加拿大
 英国/瑞士
英国/瑞士







